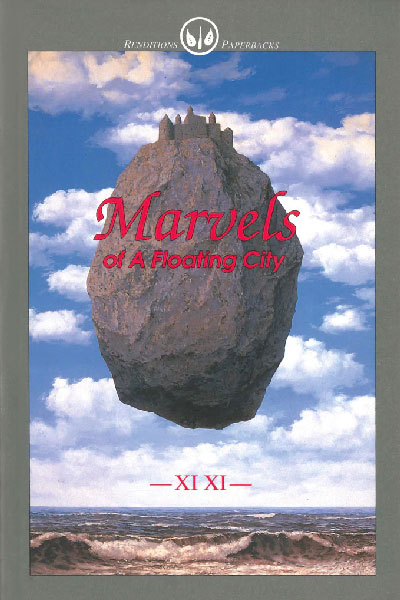美麗大廈

西西形容《我城》與《美麗大廈》這兩部發表於七十年代,同樣極具開創性的長篇小說為「一個地方的兩種寫法」。相對於《我城》的上天下海的漫遊,《美麗大廈》聚焦於一座十二層高的住宅大廈。如果城市的發展,由自帝國主義的侵佔,以及維希留所關注的速度的暴政,在《美麗大廈》裡,西西則以「極慢速」的筆法,致力為小市民自力經營的日常作傳。有別於《我城》「在地」的年輕人視角,《美麗大廈》更多的著眼於香港這座移民城市的混雜性,並關注流動的人口,以及他們的交往與互動。在大量新移民湧入的城市裡,並非某一英雄,而是眾數的「陌生人」成為了主角。作為七十年代香港的一個側面,《美麗大廈》所要勾劃出的,乃由這些陌生人自創的公共空間。
這裡的文字選自《美麗大廈》的第六章。大廈的電梯剛壞了,居民在公共空間(如樓梯、管理處)有更多相遇的機會。西西細緻描寫了他們的肢體動作、對話和物質生活,展示了城市各種居民(從兒童到老人,從人類到動物)的一個生活切片。
《美麗大廈》 第六章(選段)
興記的夥計必須把身子偏側一下才能自店中的一張小矮櫈後走出來,坐在小矮櫈上的是興記老闆的孩子,裹在一件鮮色的尼龍厚衣內,把手擱在木椅上的簿面,這簿亮出全頁的大方格,第一行橫列了紅筆書寫的字頭,包括草蜢和蝴蝶、工作和遊戲。兒童握着鉛筆極低的筆端使勁地寫字,他寫了一直行的虫,然後回轉來在虫邊加上古,最後才在極邊緣的空間寫上月。每個字都寫得出了格,由於鉛筆不再尖削,使字的筆劃粗糊如同素描的線條。他寫完了一行蝴又寫了一行蝶,即停下來,翻開課本看印刷得花彩的蝴蝶和一身青綠的草蜢。
興記的夥計把一個大紙盒擡了出門外,又從矮櫈後面跨過去取另外的一個米袋。經過小孩的時候,他也瞧了一眼滿是圖畫的課本,又看看作業的本子。
快些寫字呀,老師有沒告訴你學學草蜢,不要懶惰?
強叔叔,你是不是草蜢?
我當然是草蜢。
我爸爸呢,媽媽呢,是不是也是草蜢。
他們也是草蜢,全世界的人都是草蜢。
他挽了那個米袋走到店門外面去。興記的老闆正在行人道上攤曬一地銀白肚皮的小魚。魚都鋪在剪拆開的麻包袋面,他彎了腰蹲在路邊用一隻木筷把小魚撥散。陽光照在他的背脊,使他曖懶得不願移動到陰暗的地方去,這是少見的晴麗無風的日子,他幾乎想端一張摺椅到魚乾的旁邊坐下來。在店門的那一邊,連接着關上了半邊鋪的空運公司,裏邊依舊靜肅如同休假的課室,聲音都從數間鋪位外的輪胎店那面傳來。幾名衣着襤褸富流浪色彩的青年蹲在門口逗弄一條肥胖蠢鈍的黃狗,把一團紗線叫狗咬,彼此拖拖絆絆地糾纏。車行道側此刻停泊着兩輛花斑的汽車,其中一輛是已失去車子形態的鐵殼,沒有玻璃也沒有車頭的機器,全身像剪過毛的綿羊,一片白一片紫紅,又有一點橘子皮的條紋,彷彿有人在車上塗滿了雪花膏。另外的一輛車卻像一件巨大的手工,全車鋪滿了新聞紙,讀讀也可以消磨一個下午。坐於空運公司門前剪線頭的女孩忙於一成不變的操作,協助她的年長的親人則把墨藍的厚布褲綑紮堆在手推車上。
數數一共是幾打?
這裏是二十六打,連剛才交的一共是五十打。
你現在看着阿美,我去交貨。
婦人推着手推車在行人道上走,經過興記的門口,她打着之字路途行進,閃避開一地的銀魚。興記的老闆被一個電話的聲音喚進店內,吚喔地回應着,放下聽筒後不禁歎了一口氣。
又要送石油氣,電梯壞了這麼多天還沒有修好,一天到晚爬幾十層樓梯,鐵做的人也爬壞了吧。阿強,你今天已經上過去幾次?
八次。有五次是過了七樓。
我也走了六次。這次再由我上去吧,如果等下又有電話叫石油氣或叫米,就說明天才有民力送,要不然,請他們自己下來拿。
老闆進入店內的後座,擡了一筒石油氣出來,經過小孩的旁邊,叫他站起來讓讓路。小孩的簿子上顯出一行小艇,卻被課本蓋住了。他看着父親跨過矮櫈,擡着銹紅的重物。
爸爸,你是不是草蜢?
什麼草蜢?快些寫字。
進入大廈的管理處,你和迎面而來的興記老闆點首,管理處如今比往日逼擠,靠牆的一邊停着一輛木頭車,從焦炭火痕跡來觀察你可以認出那是賣麵婦人的車子。自從電梯失靈之後,這車子不知如何被移下來,不再回上去了,祇每晨從牆邊推出去,午後又回到同一的地方。因為車輛的體積,電視的畫面被割切了一半,常常只有一隻眼睛半個嘴巴在熒幕上閃動。電梯的前面不再出現重厚的人牆,靜止如石立的軀體均變作移動的河流,穿梭於一條蛇形的窄道,人河幾乎是不息的,一來一往,自樓梯間相對而行。有時候,兩個人在甬道中相碰,忽然同時踏向共一的方向,堅持兩個回合才分開,通常人羣都依循範式,靠牆或靠扶手的一邊,一個跟着一個。有時候,某人獨自踢踢躂躂地走下來,鬆出一口氣,也有時成羣人操步如一排兵,年幼的小童奔躍跳動,年長的都步履蹣跚,而登梯者的臉面掛上愁容,緊皺着眉眼。你隨着興記的老闆步上樓梯,彷若自己是一隻忙碌覓食羣中的螞蟻。
電梯已經壞了許多天了,這是一件和電流完全無關的事情。人們把電梯門打開,把梯箱吊扯到頂樓,推了一座機器進去,修理過許多次,依然毫無成績,據說是需要來一次大修理:整飾鐵銹,更換吊纜,重裝線路。在樓梯上步行的時候,你可以聽得牆的另一邊敲擊的聲浪,一下下的混和急驟的電鑽刺耳的震盪。樓梯上並沒有燈火,每個人都幾乎手握一把電筒,沒有照明工具的人則混在人叢中,越過黑暗的水泵房。每一層樓都有離去或前來參與的人眾,一種新陳代謝的交替。不過是幾日的時間,你可以覺察樓梯的階級已經發黑,牆面也陷下斑痕,於轉角處或梯臺,散落有瓜子殼和撕破了的紅封袋,並且間或有一段乾謝了的桃枝。由於數目之眾多,樓梯間的人極自然地均分為兩半:近欄杆扶手的一邊作為上行,附牆一邊則相反。和你一起朝上走的人行進的速度比較緩慢,你看不見最前面有什麼人,祇知道有一名大個子掏出一包煙掘出似乎是最末的一根而把紙包揑作一團隨手拋在地面,接着取出火柴,把厚如巨木的軀體橫樹於通道,擦擦地劃亮了火柴點煙。經此停頓,使後面的人都滯停在梯間款待而隊首的一干人則去得遠了。於這中斷了的行伍中,該抽煙者竟成了帶隊者,祇見他吐出一團灰霧,將火柴揮棄於梯角。稍後途經該處的人,良久仍見到閃閃金星以及裊裊旋擺的黑煙。跟在該人背後的是一名把衣袖捲推於上臂的婦人,雙手拖曳着一個極大的膠袋,矇矓中可見一團金黃色如麥桿的線狀物事,猶似一袋擠壓了的數百個假髮。婦人雖則攜帶了如此大體積的膠袋,卻費了不大的勁,彷彿那是一綑木棉花,在梯級上一跳一蹦地被拖上去了。於婦人背後,緊跟着兩個十歲左右的小童,各自抱着一個較小的膠袋,其中一個裝滿了塑膠玩具的頭,連着一道可以鎖扣他物的頸項。所有的頭皆光禿無髮,有模型鑄刻的鼻子及嘴巴,頭內已嵌配上眼睛,能夠緩緩轉動,由於被胡亂投擲於袋中,頭與頭皆滾在一起,眼睛經過震盪,有些離了框位而反了白,亦有部分的眼斜窺在一角,作種種奇異的瞥視。另外的一個袋中則堆滿塑膠的肢體,全部是手和腳,每一隻手都一模一樣,同色同形同等大小及長短。小孩們一邊走一邊戲耍,嘴裏吹出一個白球,然後卜的一聲爆破再把白球的殘殼翻入嘴內咀嚼。
做完這一袋公仔,我就有兩塊錢了。
我比你多,我有兩塊半。
我去買一枝水鎗。
我去買一條軟綿綿的蛇,可以嚇同學。
明天好像要測驗英文。
怕什麼,最多又吃雞蛋。
走在小童背後的是興記的老闆,他以一邊肩及一隻手托着一筒石油氣,另外的手中握了兩個圓扁罐,當他把手鐘擺式晃動時,你可以看見罐側繪了一條魚。你並不清楚走在你背後的共有多少人,聽腳步的聲音絡繹不絕,在梯道的轉彎,你見到一名小食肆中送外賣的老人,挽着灰白的銻盒,然後是兩名年輕的女子,均穿上熨斗式高鞋,在梯級中走動着一類踩高蹺的演技。經過水泵房之後,梯間光亮起來,有人自樓層橫插,切斷了隊伍匯入下行的人龍中,其中一人背着一綑花棉襖,亦類似一名耍雜技的賣藝人。於三樓上,有一健碩男子把眾人都截停了,無論朝那一個方向行進的人都被請入梯角,並肩擠站。
對不起,對不起,很快的。
不要是打劫呵。
立於梯間之中年男子朝上層喊了一聲,祇聽得一陣澎隆澎隆的響聲,自梯上滾下一球一球的布袋。其中一個袋透明,露出內裏圓圓的紗線和滾軸,這般的囊袋一下子滾下了十多個,被樓下的人火速推踢拖拉曳堆在梯側的空間。從樓上奔下一人亦伸手操作,又有一人提着輛四輪的小鐵車,車柄及推手的部分都被摺起靠貼在車身的方格枝條上。搬運紗團的人連聲致歉,眾人有等爭先搶着上下梯層,亦有人稍作歇息。從底下上來的人,遲來的反而先啟程了,提着食物盒的外賣老者亦細心地步上樓梯。手抱塑膠玩具碎片的小童把膠袋放在梯級上推滾上去,推了五級光景即把袋依舊提抱,老老實實行走,嘴巴前面仍吐出一個珠子似的白球。一雙夫婦在這中間的驛站轉換他們手內的負擔,年輕的妻子把懷抱的嬰兒連披肩被帶交給丈夫,即時接替男子手中的提袋,袋的拉鍊已經膨脹得扯不上,袒出摺疊的布幅及瓶罐。嬰兒睡熟了,在手的交替中並不曾醒轉,母親伸手把包裹嬰兒的衣物整理妥停,又撥開遮蓋嬰兒臉面的巾帽,才跟着丈夫一起上樓去。經過一次阻隔,樓梯上更形忙碌起來,部分的人仍滯留在梯道的轉折處,從上層下來的人如一支趕集的馬隊,響起一梯的喧嘩。
啊,興記老闆,你也在這裏,可不可以替我們送一罐火水上來?還要半打雞蛋。
如果不是等着用,明天行不行?
好的,明天吧,記不記得我住那裏?十二樓二座。
一罐火水,半打雞蛋。十二樓二座。
興記的老闆把放在地面的石油筒提起,作舉重之姿勢托於肩上,這肩膊如今沾上一層花白的牆粉。你仍走在他的背後,在他的前面是穿着熨斗鞋的女子,正在商量要不要購置一雙高跟的長統靴,伊自電視中曾見某些於潮流中翻滾之女人作瞬息不一之打扮,於臨近的日子皆無一不把條粗布褲捲疊至膝際成為風尚。其中一名女子則徵求友伴之意見,於來臨之夏日將換穿一襲歐洲色彩之泳衣。
在四樓之上,女子轉入樓層去了。沒多久,亦不知是後者之腳程快還是前者之步履慢,興記的老闆已緊隨年輕夫婦之後。你甚至可以聽得那家庭中之主要成員在討論柴米油鹽,經濟上之增支及月結之赤字,主婦之腳步益見沉重了。自梯上下來的人,有認得興記老闆的都和他點首打招呼,彷彿他是一架勤奮的運輸車。他則一面應對着一面低下頭,似乎繼續交談兩句即會增加搬運的次數。因此,到了稍後,他以石油筒,擋住了視線,不再和任何人的眼睛接觸,同時自顧說着無可奈何的怨語,如同獨個人於戲臺上唱了一段主題曲。
生意好像十分興隆啦,果然是名副其實的興記囉,阿貓也叫一罐火水,阿狗也要送一筒石油氣,其實呢,不外是想找個人做送貨員,免得自己下樓去買。要火水,石油氣是假,要罐頭雞蛋紙麵是真。天氣這麼冷,居然有人叫半打汽水,順便送兩隻皮蛋,三罐午餐肉,一塊榨菜,五毛錢粉線,一罐鳳尾魚,一罐粟米,兩罐青豆,兩斤黄片糖,半斤紅豆,晚飯的菜和消夜都有着落了。如果是平日,明知是麻煩的事情,也就算數,偏是電梯壞了,這種生意怎麼做?越是住得高的人越是叫得勤,紙包麵噢,鹹酸醬噢,十一樓。齊眉噢,蠔油噢,十二樓,又不見住在二樓的人來喚米喚油。
喂,興記的老闆,又要御駕親征麼?
可不是,我倆可真是同病相憐哪。
你們這層樓怎麼攪的,電梯壞了這麼多天還沒修好,害得我每天跑上跑下。雖然說,郵袋可以放在管理處,但是十多層樓呢,一封掛號信,數百級樓梯,碰上收件人不在家,全層樓沒有半個人來應門,第二天又得走一趟。這樣派信法,我寧願一年都是十二月了。算起來,十二月還有津貼,現在可連鞋子也要賠上一雙才行。
興記的老闆和郵差擦肩而過,前者閉上嘴悶着聲,後者卻叨叨嘮嘮作念經式獨白彷似一名學童背誦課文,又像流徙的浪人無意識地吟說。繼續步行兩層樓梯,數量不眾之小羣人均站於梯臺歇息,興記的老闆亦步向人叢,將肩上之重負暫且擱下。你腿足的麻酸登時濃起來,竟追隨着前行者的履跡而停頓一隅。經過片刻的休息者自你等身邊離走,梯道間仍盈滿兩道流動之人羣,站在轉角的凹口。你目擊這一支不尋常之隊伍,沉默中蘊含不耐及煩憂,容貌一一反映出身心之困頓。你從來不曾見過如此眾多的頭臉,其五官之組成皆非陌生,有些在電梯內出現過,有些曾圍聚於管理處,除了幾張小童稚氣的臉仍保持一貫的明朗外,一般的表情都趨向陰暗了。是在這憑藉雙足走動的時刻,你發現各人負荷的沉重,有上半的人手中持物,或雙臂抱托着不能捨棄的東西;一人肩擔着數十根赤皮的甘蔗自梯上下來,在轉角處仔細衡量物體之長度,終於不免把蔗根的黑泥掃了一抹於牆上。從樓下上來的一人則舞動着兩根極長的晾衣竹,竹上套着一紅一綠的膠套,他一壁走一壁不住把竹端朝梯頂的空隙探伸,也把樓頂的牆粉刷得掃了一地。因此,自梯角轉下來的一名女子不得不用手扇撥灰粉,同時拂拍頭髮和衣襟。跟在她背後的一人,雙手捧着一個大碗,碗上覆蓋了一隻碟,碟上一隻小醬油容器面浮上了粉屑,顯然不能用了。持竹的男人是身健體碩的大漢,相貌威嚴而帶煞氣,拿食物下樓的人一句話也不說便默然走了。反而是緊跟持竹大漢之後的胖婦人喊叫了一陣:喂喂,是不是拆樓呀。她兩隻手都提拎着膠桶和銻鍋,裏面盛載大批油膩的碗筷,每踏步一級,隨身搖晃一串噹啷的陶聲。在樓梯的轉角,她和站立的一干人打一集體招呼,你認得這是日出而作的賣麵婦人,銻鍋內的麵已經全數售清回來。
原來有這麼多人站在這裏。興記老闆怎麼你也走不動了麼?
沒有氣了。
沒有氣?這一筒是什麼呀?
賣麵的婦人把一隻銻鍋擱在石油氣筒的筒頸上,看看並不妥穩,又把鍋提下地,她一直咧着嘴笑,這是你於樓間所見唯一依舊能够嘻說的成人。於此時,梯間突然出現一個塑膠的浴缸,由兩個人並不特別費勁地擡上來,吸引了無數的目光,彷彿天際亮着一顆十字星。那浴缸散發着隱隱水藍幽光,經過窗孔的時候,於日照之中,透明如一塊不含雜質之中性肥皂。浴缸被斜側了推進,眾人都見到缸底有一個去水孔,缸壁上吊着一條銀鏈,鏈端埀着一朵圓橡膠栓塞,如鐘擺般左右盪晃。
這可是一個浴缸不是?
是呀,最新的出品呢。
能不能裝熱水?能不能載得起二百磅重的大個子?可以洗泡泡浴的吧?怎麼去水呢?廁所裏無論如何放不下呀?上次我們買一個冰箱,一個門的那種,要把廚房門拆了才能把冰箱搬進去。
幾多錢一個?在什麼公司買的?還有沒有別的顏色?譬如說︰粉紅?這是不是最小的?看起來很輕噢,是硬塑膠嗎?真是日新月異。是不是外國貨?
可惜沒有水龍頭。裝熱水器會不會很貴?用熱水器危險不危險?是不是用花灑可以省許多水?
洗衣服倒是挺方便的噢。
站在梯間的人有一大半跟着浴缸一起走了,嶄新的刺激使他們暫且忘卻疲勞,並且帶來論辯的話題。有幾個人開始探討煤氣與電的優劣,亦有人祇簡單的把浴缸和電視的重要性作一直接的對比,甚至不乏小童尾隨浴缸到達終站,查察一項詳細的結局。賣麵婦人的女兒自梯間出現,提着一袋新鮮的油麵和一袋半截綠半截白的豆芽,她把市場中帶回來的膠袋交給母親,轉過來挽起銻鍋和膠桶,兩個人即進入廊道去。在入口的地方,她們略一避讓,祇見年邁的管理員掃出一堆垃圾來,然後握着掃帚的長柄休息。
垃圾好像比以前多了吧,榮伯。
走廊裏倒還好,卻是樓梯。以前根本用不着打掃,整天也沒兩張紙屑,可是自從電梯壞了,清理也清理不了那麼多。
電梯不過是兩部,我在管理處站着,電梯下來時,門打開,如果有垃圾,我伸過掃把一拖就掃乾淨了。現在卻是十二層樓,每一段樓梯都是垃圾,顧得這裏顧不得那裏。
怎麼樓梯會特別髒呢,走廊也是。
你也看得見的啦,這麼多的人在樓梯上走。不過,還有一個理由,是晚上倒垃圾的緣故。以前有電梯,每層樓的垃圾由電梯搬下去,又快捷又方便,現在就不同了,垃圾籮都要從樓梯一籮一籮一級一級擡下去,速度慢了,籮裏的污水都漏出來滴在梯級上。
垃圾又多,過了年誰家沒有一堆殘花果皮豬牛骨頭,每個垃圾籮載得滿滿的,搬上搬下時自然瀉潑些出來。
倒垃圾的一家人還要辛苦,從前十點鐘來倒垃圾,一家連大帶小五口,兩個鐘頭可以把垃圾推出大門外疊好。現在從七點開始,搬到十二點也倒不完,小孩子小,那裏搬得動,全靠兩個大人,比我還要吃力。
我們應該開一次互助會討論一下。
已經提過,大概這兩天就要開了吧。
年邁的管理員說着又掃起地來,地上有發了黃的水仙花,花枝間夾着乾澀的棉花和紅紙的細環,露出粗厚的根莖,混在灰塵裏,又有一隻斷了搭帶的膠拖鞋,像一塊巨大的橡皮,卻無法把地面的污痕擦去。興記老闆肩上托着石油氣筒與賣麵的母女同時反方向起步。繼續上樓的這一刻,你跟在一名婦人背後,那婦人輕輕咳嗽使你憶記她在電梯中感冒的狀態。她的健康顯然有了進展,不過祇咳了一次即噤了聲。此刻她手中提了兩個扁平的紙盒,上面橫向列了芝麻湯糰幾個白底赤字,另外的一手則挽了一顆手臂粗細長度的天津菜,因為菜顆裹護在玻璃紙套內,菜葉沒有披散,顯得柔嫩而新鮮。她必須彎折手肘使腕部與地面平行才使菜葉的頂端不致拖曳於地面。過了樓梯的第七層,上行的人逐漸稀落,梯道也寬坦些,走在樓梯上可以不必盡量貼靠欄杆的扶手,從上面下來的人步伐則更形輕快;如果不是由於作過一次山行的踏青,攀登那道埀直的天梯,你並不會如此失勁疲乏。走在你前面的婦人行動遲緩,你亦藉此把步行的速度降至最低,如同一輛爬山的老舊汽車。興記的老闆轉入梯側的廊道去,山洞形的缺口空無人跡。當你把視線移挪,卻瞥見一團低矮的黑茸茸物事掠過,於匆忙中窄窄的裂縫間飛過一列毛腿。
那是什麼?
好像是一隻黑貓。
那有這麼大的貓。
廊道上傳來狗的吠鳴,祇聽得興記老闆趕狗的重步頓地聲以及應門的喊叫︰送石油氣的。有人開門接着又有人關門,傳出呼狗的唿哨和斥罵。樓梯上的過客更少了,隔了一段路才迎面遇見一兩個人。第九層上根本沒有人從樓上下來,然後祇有一名婦人及一名男孩,和提着菜的婦人打招呼並微笑。男孩見了熟人登時消失了下樓梯時的躍動,躲在母親的背後,擡起頭朝窗孔外面張看,他踮起足尖祇能瞥見一塊白花花的天空,對面的樓宇,在竹桿的環抱內,露出髹上橘紅色防銹劑的下水管,有幾面牆嵌上了小磚,彷彿整座樓宇是一幅浴室的牆壁。
買了湯糰阿。
我家阿媛最喜歡吃湯糰。咦,小弟弟今日不用上學麼?
說起來就醜了,上學的時候,時間趕忙了,就催他快些走,一面要穿校服一面要結鞋繩,誰知跑到樓下才知道忘記帶書包。
住在十二樓那麼高,我又是個有血壓病的人,回上來是走不動的了,叫小孩子一個人上樓開門拿書包我又不放心,結果就沒有上學,到茶樓去喝了茶,坐了一會,買了菜才回家。
小男孩依舊躲在母親背後,卻把頭埀下了,用腳踢着地上一隻很小的果實,大概是從一段桃枝上落下來的,那桃子自梯級上骨碌碌滾下去了。小男孩又伸足踏着一枚煙蒂,直踩得那煙蒂開出了一朵小黃花。提着天津菜的婦人喘着氣再走上樓梯,你轉向第十一層的廊道,平坦的走廊使你突然覺得腳底下彷彿低陷了。有兩名小童在電梯口的空間拍塑膠羽毛球,握着短棒亦為塑膠所鑄的球拍,他們擊打出兩次連續的撞碰,聲音就突然斷折了。你自廊道上緩步行來,目擊這遊戲遭到綿串的挫敗。每次拍擊不過兩個回合,球即失手墜地,他們必須一次又一次把球撿起重新擲發,彷彿所作的運動為一項拾球的競賽。然而兩名小孩都不氣餒,蹲肢彎腰,俯仰汗濕的髮額並揮揚手臂,使你把傴僂的背不自覺地挺了挺。你聽得見膠球落地的響聲,和室內運動場上的球賽隱隱謀合,但你不聞裁判的尖哨和分數的報道,亦沒有掌聲。塑膠球落在地上或牆上也會輕微地躍彈,發出堅實的躂、躂。有時球斜撞在電梯的門上,碰出空洞的迴響,安安地鳴唱。每次塑膠球落在電梯的門上,如同叩門的手,輕輕地敲打。當你站在電梯附近,小孩住了手讓道,你矇矓地認得他們居住屬於和你相同的樓層;回溯那次防盜演習,他們均站立父兄的身背探首張望,手中似乎握持這樣的物體自衛。你瞥悉他們期待的神色並靜止待發的雙手,即加速了腳步。麥嬸家的鐵閘和木門都空敞着,朝裏衹見一團背光的黑物,從視覺出發你感見一列濃密的灌木叢,延攀交纏伸展的枝枒,從嗅覺則覓得一座遍植薄荷的園林。新年已經過去,麥嬸家的門上飾品凋殘了,部份的揮春撕得七七八八,剩得一點兒紅金紙片留在警眼上端,彷如一隻獨眼獸的犀角。
©2025 - All rights Reserved. Our Xi Xi Our City.